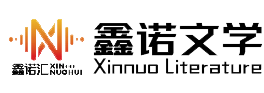老张头死了,死得极不体面。
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不到一上午就飞遍了整个清水镇。
人们交头接耳,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兴奋与鄙夷。
在这个常住人口不过三千的小镇上,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劲爆的新闻了。
"听说了吗?老张头死在刘寡妇床上了!"
"可不是嘛,据说发现的时候两人还光着呢!"
"啧啧,都六十五的人了,还这么不检点..."
"那刘玉芬比他大十几岁,还瘫着两条腿,真不知道图什么..."
镇卫生院的白色走廊里,张建军听着身后刻意压低的议论声,拳头在口袋里攥得死紧。
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却感觉不到疼。
从接到电话到现在,他的大脑一直处于一种诡异的麻木状态,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张老师,节哀顺变。"
卫生院的王会计从他身边经过,眼神闪烁,
"那个...需要帮忙的话..."张建军僵硬地点点头,没有接话。
他能感觉到对方目光中的探究和怜悯,这比直接嘲笑更让他难堪。
父亲死了,这本该是件悲伤的事,可现在,他连正常地表达哀悼都做不到。
"建军啊,你总算来了。"
派出所的李所长从走廊尽头快步走来,脸上带着尴尬的神色,
"那个...情况有点特殊,你得有个心理准备。"
张建军跟着李所长走向停尸房,水泥地面冷冰冰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响。
他今年三十八岁,是镇初中的语文老师,平日里最重体面,
可现在,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扒光了衣服游街示众。
停尸房的门被推开,一股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扑面而来。
张建军的胃部一阵抽搐。
"根据初步检查,死亡时间大约是今天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
穿着白大褂的法医掀开盖在尸体上的白布,
"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应该是在...呃...性行为过程中发生的。"
张建军的目光落在父亲那张灰白的脸上。
老张头的眼睛半睁着,嘴角甚至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仿佛死亡来得太快,连痛苦都没来得及感受。
他的脖子上还有几道浅浅的抓痕,胸口处隐约可见几处暗红色的斑点。
"刘玉芬呢?"
张建军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在隔壁病房,受了点惊吓,但没什么大碍。"
李所长咳嗽了一声,
"她说是你父亲主动去找她的,每周三晚上都去,已经...呃...持续了五年左右。"
五年。张建军在心里重复这个数字,感到一阵眩晕。
也就是说,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父亲就开始和这个比他大十三岁的瘫痪寡妇搞在了一起。
他想起父亲平时那副道貌岸然的模样——退休前是镇政府的会计,
业余时间喜欢在老年活动中心下棋、读报,谁见了不夸一句"张老师正派"?
"现场...有什么异常吗?"张建军艰难地问道。
法医和李所长交换了一个眼神。
"没什么特别的。"李所长说,
"就是...呃...现场发现了一些药物,伟哥之类的。你父亲这个年纪,用这些也正常..."
张建军突然想起上个月回家时,在父亲卧室抽屉里看到的那瓶硝酸甘油。
当时他还奇怪,父亲心脏一向很好,为什么要备这种药。
现在想来,或许早有预兆。
"我能看看死亡报告吗?"法医递给他一份文件。
张建军快速浏览着那些医学术语: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肌缺血、心室颤动...最后一行写着"性行为诱发的急性心功能衰竭"。
"需要进一步尸检吗?"法医问。
张建军摇摇头。再查下去又能怎样?让更多人知道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他现在只想尽快结束这场噩梦。
"不用了。我想尽快安排后事。"
走出卫生院时,阳光刺得张建军睁不开眼。
他的手机在口袋里不停的震动,全是妻子李红梅打来的。
他不想接,不知道该怎么向妻子解释这一切。
他们的儿子张小伟今年刚上初中,如果同学们知道了爷爷是怎么死的...
"建军!"一个熟悉的声音让他浑身一僵。
转头看见岳父李大山沉着脸站在卫生院门口,身边是眼睛红肿的李红梅。
"爸..."张建军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丢人现眼!"李大山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全镇都在看我们家的笑话!"
李红梅拉住父亲的胳膊,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走向张建军。
她的眼神复杂,既有责备,也有心疼。
"回家再说吧。"她轻声说,伸手想接过丈夫手里的文件袋。
张建军下意识地躲开了。
文件袋里装着父亲的死亡证明和遗物——一块老式手表、一个钱包和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他不敢让妻子看到钱包里那张刘玉芬的照片,照片背面还写着"给我最爱的老张"。
"我先去趟爸家里。"他说,"有些东西需要整理。"
李红梅点点头,没再多问。
他们结婚十五年,彼此之间有种默契。
但此刻,张建军觉得这默契像一层薄冰,随时可能破裂。
老张头的家在镇子西头,一栋建于八十年代的老式单元楼。
张建军用钥匙打开门,熟悉的烟草味扑面而来。
客厅收拾得很整洁,茶几上还摆着昨天的报纸和半杯没喝完的茶,
仿佛主人只是暂时出门,随时会回来。
张建军径直走向父亲的卧室。
床铺整齐,衣柜里的衣服按季节分类挂好。
他拉开床头柜抽屉,里面除了那瓶硝酸甘油,还有几盒没拆封的壮阳药和一沓汇款单。
汇款单上的收款人都是"刘玉芬",最近一张是三天前汇出的,金额两千元。
书桌抽屉上了锁。张建军用回形针捅了几下,锁应声而开。
里面是一本病历和几张检查报告。
他快速翻阅着,眉头越皱越紧。
根据这些文件,父亲两个月前在县医院做过全面体检,
结果显示除了轻微高血压外,心脏功能完全正常,根本不可能突发心梗。
张建军的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王院长"——镇卫生院的院长,他高中同学。
"建军,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王院长的声音压得很低,
"你父亲的尸检报告有点问题。"
"什么问题?"
"血液化验结果显示他体内有超量的西地那非成分,远超正常剂量。而且..."
王院长顿了顿,
"我们在他的水杯里检测到了相同成分。"
张建军的心猛地一沉:"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可能被人下了药。"王院长说,
"剂量足以诱发心脏病。当然,这只是初步怀疑,需要进一步..."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嘈杂声,然后是王院长匆忙的告别:
"我得挂了,这事你先别声张。"
张建军放下手机,感到一阵寒意爬上脊背。
他再次看向那些体检报告,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脑海中成形:
父亲的死,可能不是意外。窗外,夕阳将整个清水镇染成血色。
张建军站在父亲的书桌前,突然注意到墙上挂着的日历。
今天的日期被红笔圈了出来,旁边写着一个字:"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