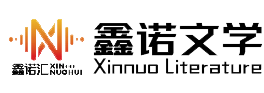张建军把父亲的体检报告和尸检单并排摊在茶几上,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
县医院的公章在灯光下泛着冷光,那行"心脏功能正常"的结论此刻显得如此刺眼。
"这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反复对比两份文件上的日期。
父亲最后一次体检是两个月前,
而镇卫生院的尸检报告明确写着"冠状动脉严重粥样硬化"。
短短六十天,一个健康的心脏不可能恶化到这种程度。
窗外传来邻居家电视的声音,晚间新闻主持人字正腔圆地播报着天气。
张建军猛地拉上窗帘,仿佛这样就能隔绝外界所有的窥探。
自从父亲的事传开后,他总觉得每一扇窗户后面都藏着好奇的眼睛。
手机屏幕亮起,是妻子发来的消息:
"小伟发烧了,今晚我和孩子在妈家住。你早点休息。"
张建军盯着这条看似平常的信息,读出了背后的潜台词:
李红梅不想回家面对他,更不想让儿子在这个风口浪尖去学校。
他能理解——今天下午校长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委婉地表示"考虑到特殊情况",
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
"我没事,"他回复道,"明天我去看小伟。"
发完消息,张建军重新审视茶几上的文件。
王院长的电话暗示父亲可能被下药,而日历上那个"药"字更是令人不安。
如果父亲真是被人害死的,那么谁会这么做?又为什么?
他的目光落在那些汇款单上。
过去三年,父亲每月都会给刘玉芬汇钱,金额从最初的五百逐渐增加到两千。
对于一个退休老人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更奇怪的是,汇款频率在最近半年明显增加,有时一个月两三次。
张建军从书架上取下父亲的记账本。
老会计出身的父亲有记录每一笔开支的习惯。
翻到最近几个月的页面,他发现除了给刘玉芬的汇款外,还有几笔去向不明的支出,
只简单标注着"药"或"检查"。
一个念头突然闪过:刘玉芬会不会知道些什么?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挥之不去。
尽管内心抗拒,张建军知道自己必须去见见这个女人——这个毁了他父亲名声的瘫痪寡妇。
清晨五点,张建军就醒了。
他做了个混乱的梦,梦里父亲站在床边,嘴唇蠕动着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窗外,清水镇笼罩在朦胧的晨雾中,远处传来早班公交车的引擎声。
他冲了个冷水澡,试图洗掉那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
镜子里的男人眼窝深陷,胡子拉碴,与平日里那个一丝不苟的语文老师判若两人。
刘玉芬住在镇子东头的平房里,那里是清水镇的"贫民区",
住的多是孤寡老人和外来务工者。
张建军把车停在百米外的杂货店门口,步行过去。
他不希望被人看见自己去找刘玉芬——光是想象那种闲言碎语就让他胃部绞痛。
刘玉芬的房子比想象中整洁,门前的小花园里种着几株蔫头耷脑的月季。
窗帘紧闭,看不出是否有人在家。
张建军站在门前,突然不确定自己该说什么。
质问她和父亲的关系?还是直接问她知不知道父亲可能被谋杀?
他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没有回应。
正当他准备再次敲门时,一个沙哑的女声从身后传来:"你找谁?"
张建军转身,看见一个瘦小的老妇人坐在轮椅上,怀里抱着一袋蔬菜。
她的头发花白稀疏,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睛却异常明亮,像两颗浑浊的玻璃珠。
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两条萎缩的腿,像两根干枯的树枝般耷拉在轮椅踏板上。
"刘...刘阿姨?"张建军嗓子发紧,"我是张建军的儿子。"
女人的表情瞬间凝固。
她手中的塑料袋掉在地上,一颗土豆滚到张建军脚边。
"进来吧。"她最终说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屋内比外面看起来更宽敞,但弥漫着一股药膏和陈旧衣物混合的气味。
张建军注意到墙角堆着几个药箱,茶几上散落着药瓶和医用纱布。
刘玉芬费力地操纵轮椅来到茶几前,示意张建军坐下。
她的动作很慢,但异常精准,显然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她直接说道,眼睛盯着自己的膝盖,"老张的事...我很抱歉。"
张建军没想到对方这么直接,一时不知如何回应。
他环顾四周,试图寻找线索——任何能解释父亲为什么会和这个女人保持五年关系的证据。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他最终问道。
刘玉芬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微笑:
"老年活动中心。五年前我刚搬来镇上,你父亲是少数几个不嫌弃我残疾的人。"
她抬起头,"不像你想的那样,我们一开始只是朋友。"
"那后来呢?"张建军忍不住追问,"为什么他要给你那么多钱?"
轮椅上的老妇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她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捂住嘴。
咳嗽平息后,她迅速将手帕塞回口袋,但张建军还是看到了上面的暗红色斑点。
"我有肺气肿,"刘玉芬平静地解释,"那些钱是医药费。你父亲...很善良。"
张建军想起汇款单上的金额。
什么样的医药费需要每月两三千?而且为什么最近半年突然增加?
他正想追问,突然注意到茶几下的垃圾桶里露出一个熟悉的药盒——
正是父亲常用的那种壮阳药。
"我爸那天晚上为什么会来?"他换了个问题。
刘玉芬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周三他都会来,帮我做家务,然后...你知道的。"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那天他说心脏不舒服,但我以为只是...太兴奋了。我给他倒了水,然后..."
她的声音哽住了。
"水里有什么?"张建军紧盯着她。
"什么?就是普通的水啊!"刘玉芬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慌,"你什么意思?"
张建军没有回答。他的目光扫过房间,在电视柜上发现了一个小药盒,
上面贴着"睡前一片"的标签。正当他想走近看清楚时,刘玉芬突然剧烈咳嗽起来,这次比之前更严重,整个人都在颤抖。
"药...药..."她指着沙发上的手提包。
张建军赶紧过去翻找,摸到一个喷雾剂。
他递给刘玉芬,看着她深吸了几口,呼吸才渐渐平稳。
"你需要去医院。"他说。
刘玉芬摇摇头:"没用的,晚期了。"她苦笑一下,
"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纠缠你们家多久。"
这句话让张建军心头一震。一个垂死的女人有必要谋杀她的情人吗?除非...
"我爸知道你的病情吗?"
"知道。"刘玉芬的眼神黯淡下来,
"所以他最近来得更勤了,还帮我付了特效药的钱。那药很贵,但能减轻痛苦。"
这解释了汇款增加的原因。
张建军感到一丝愧疚,但很快又想起王院长的话。
如果父亲真是被下药的,那么最后一个见他的人就是刘玉芬。
"我能看看你吃的药吗?"他突然问道。
刘玉芬愣了一下:"为什么?"
"只是想了解一下。"
张建军尽量使语气显得随意,
"我爸最近也在吃一些药,我担心会不会有冲突..."
刘玉芬犹豫片刻,还是指了指电视柜上的药盒:"大部分在那里。"
张建军走过去,仔细查看那些药瓶。
大多是治疗肺气肿和止痛的药物,但有一个小棕瓶没有标签。
他刚想拿起来看,刘玉芬突然说:
"那是安眠药,医生开的。我晚上疼得睡不着。"
张建军点点头,趁她不注意,快速用手机拍下了所有药瓶的照片。
当他转身时,发现刘玉芬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既像是怜悯,又像是恐惧。
"你长得真像他,"她轻声说,"尤其是皱眉的样子。"
这句话不知为何让张建军鼻子一酸。
他想起父亲总说他太爱较真,一点小事就皱眉。
现在父亲不在了,而他甚至不能公开哀悼,因为那死亡太过耻辱。
"我该走了。"他突兀地说,
突然无法忍受这个充满药味的房间和那个看他的眼神像看另一个人的老妇人。
刘玉芬没有挽留。
就在张建军走到门口时,她突然说:
"你父亲是个好人。不管别人怎么说,记住这一点。"
张建军没有回头,只是点了点头。
关上门后,他深吸几口新鲜空气,试图理清思绪。
刘玉芬看起来确实病重,而且似乎真心怀念父亲。
但她对那晚细节的回避和某些药物的隐瞒,又显得十分可疑。
更重要的是,如果父亲的心脏真的健康,那么尸检显示的严重病变从何而来?
长期下药?一次性大剂量?谁会这么做?
张建军刚走到车前,手机响了。是岳父李大山。
"建军,马上来家里一趟。"李大山的语气不容拒绝,"红梅有事跟你说。"
张建军的心沉了下去。
他知道那是什么事——从昨天开始,李红梅就一直在暗示他们需要"分开冷静一下"。
在这个小镇上,分开冷静往往意味着离婚的前奏。
二十分钟后,他站在岳父家宽敞的客厅里,面对眼睛红肿的妻子和面色铁青的岳父。
小伟的房门紧闭,里面传来低沉的游戏音效。
"我受不了了,建军。"李红梅开门见山,声音颤抖,
"今天去菜市场,所有人都在指指点点。王婶甚至问我...问我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癖好。"
李大山重重地拍了下茶几:
"丢人现眼!我在清水镇活了六十年,从没这么难堪过!红梅和小伟不该受这种罪!"
张建军握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他想辩解,想怒吼,想说他父亲可能是被谋杀的,
但现在说这些只会让妻子更觉得他疯了。
"你需要什么?"他平静地问李红梅。
"分居一段时间。"李红梅不敢看他的眼睛,"我带小伟回娘家住。等这事...平息了再说。"
张建军点点头,心如刀割。
他知道在这个小镇上,没有什么真正能平息的事。
父亲的死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永远的谈资,而他的家庭将永远带着这个污点。
"我理解。"他说,然后转向岳父,"爸,能让我跟小伟说几句话吗?"
李大山哼了一声,算是默许。
张建军轻轻敲开儿子的房门。
十二岁的张小伟坐在床上玩手机,眼睛又红又肿,显然刚哭过。
看到父亲,他迅速低下头。
"爸,爷爷真的是那么死的吗?"
孩子突然问道,声音里带着与年龄不符的疲惫,"学校里都在传..."
张建军在儿子身边坐下,斟酌着词句:
"爷爷是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其他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记住爷爷很爱你。"
"可是他们都说..."
小伟的声音哽咽了,
"小明说我以后也会变成那样,还给我起外号..."
张建军一把抱住儿子,感到小小的身体在他怀里颤抖。
这一刻,他对那些散布流言的人、对这个闭塞的小镇、
甚至对死去的父亲都涌起一股强烈的恨意。
"听着,儿子,"他捧起小伟的脸,
"别人说什么不重要。你是张家的孩子,要抬起头做人。
明天就去上学,谁敢笑话你,就直视他的眼睛,问'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张建军知道这些话对一个孩子来说太过沉重,但他别无选择。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要么挺直腰板,要么被彻底压垮。
离开岳父家时,天空开始下雨。
张建军站在雨中,任由冰凉的雨水打湿衣服。
他突然想起小时候有一次被同学欺负,父亲也是这样站在校门口等他,
然后牵着他的手走回家,一路上一句话都没说,但那温暖的手掌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现在轮到他来守护这个家了,
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出父亲死亡的真相——无论那真相有多么丑陋。
他掏出手机,拨通了王院长的号码:
"关于我爸的尸检,我需要知道更多细节。还有,能不能帮我查查刘玉芬的用药记录?"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你确定要查下去?有些事...可能知道了反而更痛苦。"
张建军看着雨中模糊的街景,声音坚定:
"我必须知道。为了我爸,也为了我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