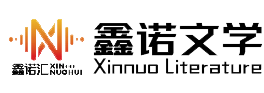1972年,夏,红星生产大队。
汗水顺着林晚(重生后名字)瘦削的下颌线滑落,
滴进脚下刚割下来还带着泥土腥气的猪草筐里。
正午的日头毒辣辣地晒着,田埂上的知了叫得人心烦意乱。
她直起酸痛的腰,用手背抹了把额头的汗,粗糙的触感提醒着她,这不是梦。
眼前是熟悉的、略显破败的村庄土路,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属于集体的翠绿稻田。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青草和隐约的农家肥味道。
一切都真实得让她心头发颤,也沉重得让她几乎喘不过气。
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1972年,养父母一家都还在的时候……
这个念头像烙铁一样烫着她的心。
她低头看着自己那双布满细小伤痕和老茧、指节粗大的手。
这双手,前世曾因为嫌弃农活粗鄙,沾了点土就大呼小叫,甚至以此为借口,
把脏活累活都推给老实巴交的养父母和年幼的弟弟妹妹。
最终,也是这双手,因为贪婪和愚蠢,间接……不,
是直接地,把真心待她的一家人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前世那短暂又罪恶的一生,如同最恐怖的噩梦碎片,瞬间涌入脑海。
她叫林薇薇,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
莫名穿到了六十年代这个也叫林晚的小姑娘身上。
仗着“穿越女”的“先知”和几分小聪明,她看不起这个贫穷落后的家,
看不起只会埋头苦干的养父林大山和总是默默操持家务、省下口粮给她吃的养母王桂香,
更看不上那两个总是跟在她后面怯生生叫“姐姐”的拖油瓶弟妹。
她觉得憋屈,觉得老天爷亏待了她。于是,她开始“作”。
她利用一点点“先知”信息,投机倒把,偷偷摸摸。
起初只是为了给自己弄点好吃的、好穿的。
但贪婪的种子一旦种下,便疯狂滋长。
她开始不满足,想要更多,想要离开这个“穷窝”。
她听信了隔壁大队那个油嘴滑舌、号称有门路的王麻子的蛊惑,
参与了一桩极其危险的“大买卖”——盗卖集体的粮食。
养父林大山是生产队的老实会计,一辈子清清白白。
她为了掩盖自己参与盗卖的事实,也为了在王麻子许诺的“大好处”里多分一杯羹,
竟然……竟然在关键的账目上做了手脚,
把巨大的亏空巧妙地转嫁到了毫不知情的养父头上!
东窗事发。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公社的革委会带着人冲进林家,翻箱倒柜。
养父林大山看着被“铁证如山”指认的账本,那张布满风霜的脸瞬间惨白,
他难以置信地看向自己这个“有文化”的养女,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养母王桂香哭喊着扑上去解释,被粗暴地推开。年幼的弟妹吓得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贪污集体财产”、“挖社会主义墙角”、“坏分子”……一顶顶沉重的大帽子扣下来。
林大山被带走,游街,批斗。
巨大的耻辱和冤屈压垮了这个耿直的汉子,
他没能熬过那个冬天,在一个寒冷的夜里,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悲愤的生命。
养母王桂香受不了打击,一病不起,不久也撒手人寰。
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大的才十岁,小的七岁,
在亲戚的嫌弃和白眼中艰难求生,最终……也未能长大。
而她,林薇薇,拿着王麻子分给她的那点蝇头小利,以为能远走高飞,
却在逃跑的路上被愤怒的村民抓住。
她的“穿越女”光环在绝对的愤怒和时代的洪流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等待她的,同样是批斗、游街、劳改……最终,在绝望和病痛中,
她死在了阴暗潮湿的牛棚里。死亡,并非解脱。
她坠入了地狱。那并非神话传说中的刀山火海,而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冰冷和永恒的孤寂。
她一遍遍“观看”着自己犯下的罪行:
养父林大山被批斗时绝望的眼神,养母王桂香病榻上无声的泪水,
弟妹们蜷缩在破屋角落冻得发紫的小脸……
她清晰地感受到他们临死前的痛苦、冤屈和对她的恨意!
这些情感化作实质的业火,焚烧着她的灵魂,让她痛不欲生,却又求死不能。
那种灵魂被撕裂、被业火反复灼烧的痛苦,比肉体上的死亡恐怖千万倍。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瞬,也许是永恒。
一个冰冷而宏大的声音在她意识中响起,带着审判的意味:
“罪孽深重,业火焚身。念汝受刑中尚存一丝悔意,予汝一次赎罪之机。
重归孽起之时,消尔业障,偿尔血债。若再蹈覆辙,业火永随,魂飞魄散!”
紧接着,是无尽的混沌和坠落感……
再睁眼,她就回到了这里,
1972年的夏天,养父母都还健在,弟妹还围着她叫“姐姐”,悲剧尚未发生的时候。
她变回了那个十五岁的林晚,一个刚刚初中毕业、即将面临回村务农命运的普通村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