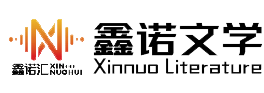就在这时,王麻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目光有意无意地向门口扫了一眼。
林晚心头一凛,立刻缩回身子,后背紧紧贴在冰冷的土墙上,大气不敢出。
黑暗中,她只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和屋里隐约的交谈声。
王麻子那阴鸷的一瞥,像毒蛇的信子舔过她的皮肤。
她回来了,带着地狱的业火回来了。而她的敌人,也早已在黑暗中露出了獠牙。
赎罪的路,从来不是坦途。守护这个家的战斗,在她重生的第一天,就已经悄然打响。
林晚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嵌进肉里,眼中燃烧起决绝的火焰。
这一次,她不再是那个愚蠢贪婪的猎物,
她要成为守护者,哪怕拼上这条命,也要把王麻子和他的阴谋,一起拖进地狱!
夜色,更深了。堂屋小窗透出的那点昏黄灯光,
在林晚眼中,成了这场无声硝烟的第一道烽火。
堂屋小窗透出的昏黄灯光,像一只不怀好意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贴在墙根阴影里的林晚。
王麻子那最后扫向门口的一瞥,带着毒蛇般的阴冷和探究,
让她浑身汗毛倒竖。她屏住呼吸,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撞碎肋骨逃出来。
前世被欺骗、被利用、最终被当作弃子推向深渊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她淹没。
不能慌!林晚,你不能慌!
她在心底对自己嘶吼,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尖锐的疼痛让她混乱的大脑强行找回一丝清明。
前世地狱业火焚身的痛苦远比此刻的恐惧更甚!为了守护这个家,她必须冷静!
屋里的谈话声压得更低了,断断续续,听不真切。
王麻子那油滑的声音偶尔拔高一点,似乎在解释着什么,而父亲林大山则多是沉闷的“嗯”、“哦”回应,偶尔夹杂着翻阅账本的沙沙声。
林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账本!王麻子的目标果然是账本!
他到底在做什么手脚?是已经开始在工分记录上做文章,还是在试探父亲的态度?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林晚后背紧贴着冰冷的土墙,初秋的夜风带着凉意钻进她单薄的衣衫,
她却感觉不到冷,只有手心不断渗出的冷汗和几乎要跳出喉咙的心跳。
终于,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传来,接着是王麻子刻意拔高的、带着谄媚的笑声:
“……行,大山哥,那就这么着!这工分的事,您多费心!
我也就是瞎操心,怕大伙儿闹意见,耽误了生产队的进度不是?
您是老会计了,有您把关,我放一百个心!”
“嗯,晓得了。”
林大山的声音依旧沉闷,听不出太多情绪。
脚步声响起,朝着门口来了!
林晚瞳孔一缩,像受惊的兔子般,用尽全身力气,
悄无声息地退到院子角落那堆码放整齐的柴垛后面,将自己瘦小的身体完全缩进浓重的阴影里。
吱呀——门开了。
王麻子矮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并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站在门槛上,
左右张望了一下,那双在夜色中显得格外亮的三角眼,如同探照灯般扫过寂静的小院。
他的目光在柴垛方向停顿了一瞬。
林晚死死捂住自己的嘴,连呼吸都停滞了,身体僵硬得如同石头。
她能感觉到那道目光像冰冷的针,刺在她藏身之处。
好在,王麻子似乎没发现什么异常,他嘿嘿干笑了两声,对着屋里说:
“大山哥,那我走了啊!您早点歇着!”
说完,才转身,脚步轻快地消失在村道的黑暗中。
直到那脚步声彻底远去,林晚才敢大口喘息,冷汗早已浸透了她的后背,
夜风一吹,冷得她打了个哆嗦。她扶着柴垛,腿脚有些发软。
他刚才……是在看我藏身的地方吗?他是不是怀疑了?
这个念头让她遍体生寒。
王麻子此人,心狠手辣又极其多疑,前世能成功陷害父亲,靠的就是这份阴险狡诈。
自己刚才的窥探,很可能已经引起了他的警觉!
他一定会加快动作,或者……改变策略,直接针对自己?
危机感如同冰冷的藤蔓,瞬间缠绕住她的心脏,比刚才更甚。
她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弄清楚王麻子今晚到底做了什么!
林晚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摸到小屋门口。
父亲林大山还坐在煤油灯下,对着摊开的账本,
眉头紧锁,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发出沉闷的“笃笃”声。
昏黄的灯光将他佝偻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显得格外沉重和疲惫。
“爹?”
林晚轻轻敲了敲门框,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
“这么晚了,还在忙啊?”
林大山似乎被惊了一下,猛地抬起头,
看到是林晚,紧绷的眉头稍稍松了一些,但眼神深处依然带着挥之不去的忧虑:
“哦,晚丫头啊。还没睡?
没啥事,就是……隔壁王会计过来对一下工分,有点小出入,我再看看。”
他含糊地解释着,下意识地用手压了压桌上的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