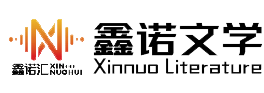那靠近的脚步声猛地一顿,随即方向一转,伴随着一声低低的、带着惊喜的咒骂:
“嘿!好肥的野鸡!别跑!”
脚步声迅速朝着野鸡逃窜的方向追去,很快消失在密林深处。
林晚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后背的冷汗已经彻底湿透了衣服,
夜风一吹,冷得她牙齿打颤。是那只突然出现的野鸡救了她!是老天爷给她的机会!
她不敢再耽搁,迅速检查了一下背篓。
金线莲被厚厚的猪草和野菜盖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不出丝毫异常。
她立刻起身,顾不上手臂和腿上的划伤,也顾不上山路崎岖,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朝着山下狂奔。每一步都带着劫后余生的惊恐和后怕。
回到村口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生产队上工的哨子声远远传来。
林晚强作镇定,放缓脚步,装作刚从自留地割猪草回来的样子。
她低着头,尽量避开人多的路,心跳依然快得厉害。
“哟,晚丫头,一大早跑哪儿去了?瞧这一身泥!”
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是同村的快嘴刘婶,正挎着篮子去自留地。
林晚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挤出一点疲惫的笑容:
“刘婶早。去后山割猪草了,路滑,摔了一跤。”
她指了指背篓上面沾着露水和泥土的猪草。
“后山?那地方可深,你个小姑娘家胆子不小。”
刘婶狐疑地打量着她沾满泥土、划破口子的裤脚和手臂上细密的血痕,
“割个猪草能弄成这样?”
“猪草少,就想着往深处走走。”
林晚低下头,声音带着点委屈,
“谁知道路那么难走……下次不敢了。”
她这副狼狈又带着点后怕的样子,倒是打消了刘婶一些疑虑。
“行了行了,快回家收拾收拾,看你这样儿!小心你娘念叨!”
刘婶撇撇嘴,不再多问,扭身走了。
林晚松了口气,快步朝家走去。推开院门,正碰上准备去上工的父亲林大山。
他看到女儿一身狼狈,也是眉头一皱:
“咋弄成这样?”
“割猪草摔沟里了。”
林晚赶紧解释,把背篓卸下来,
“爹,您快去上工吧,别迟到了。我收拾一下就去。”
林大山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看女儿确实只是皮外伤,没再多说什么,扛起锄头匆匆出门了。
弟妹也早已去了村小学。
院子里只剩下正在晾衣服的母亲王桂香,又是一阵压抑不住的咳嗽。
“晚丫头?你……”王桂香看到女儿的样子,心疼地走过来。
“娘,我没事,就摔了一下。”
林晚连忙扶住她,岔开话题,
“您快坐着歇歇,衣服我来晾。”
她把母亲扶到院里的石凳上坐下,自己麻利地晾起衣服,
眼睛却时刻警惕地留意着院门外的动静。
刚才刘婶的盘问和父亲的目光,都让她心有余悸。
金线莲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必须尽快处理掉!
晾好衣服,林晚借口要清洗伤口,把背篓拎进自己小屋,迅速关好门。
她小心翼翼地拨开上面的猪草和野菜,露出底下用苔藓包裹、品相完好的金线莲。
淡淡的、带着泥土气息的草药香弥漫开来。
她数了数,一共十七株。这已经是她力所能及、且能安全携带的最大数量了。
下一步,如何变现?
公社卫生所肯定不行,那里的赤脚医生未必识货,就算识货,也不可能给她钱,只会充公。
唯一的途径,就是县城!而且是县城里那些藏在暗处、见不得光的“黑市”!
风险巨大,一旦被抓,后果不堪设想。但为了母亲的命,她没有选择。
她需要一个合理的进城理由。
林晚的目光落在墙角那几件需要缝补的破旧衣服上。有了!
“娘,”
林晚走出小屋,对坐在石凳上缓气的王桂香说,
“我想去趟县城。”
王桂香一愣,随即皱眉:
“去县城?干啥?那么远,路费也不便宜。”
“娘,您看,”
林晚拿起一件破得厉害的褂子,
“这些补丁我快没布头了,颜色也对不上,补得难看死了。
我想去县里供销社看看,有没有便宜的碎布头或者染料,
顺便……也看看有没有便宜点的止咳药。”
她最后一句声音放低,带着恳求。
提到药,王桂香沉默了。她自己的咳嗽自己知道,越来越厉害,夜里常常咳得睡不着。
女儿突然的懂事和坚持,让她心里既酸楚又有一丝微弱的希望。
“……那,那得花多少钱啊?”
王桂香的声音带着犹豫和心疼。
“娘,我有办法!”林晚连忙道,
“我攒了点……嗯,以前省下来的零花钱,还有……帮刘婶家纳鞋底,她给了我一点粮票,
我换成钱就行!够路费和买点碎布头了!”
她急切地编着理由,生怕母亲不同意。
王桂香看着女儿殷切的眼神,再看看自己咳得发白的脸色,
最终长长叹了口气,从贴身的旧手帕里摸索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塞到林晚手里:
“拿着,穷家富路。路上小心点,别乱花钱,买了东西就赶紧回来。”
她顿了顿,又低声嘱咐,“……要是真有便宜点的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