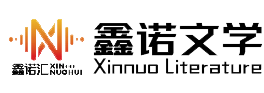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娘,您放心!”
林晚握紧那几张带着母亲体温的毛票,鼻子一酸,用力点头,
“我一定给您带药回来!”
这钱,她一分都不会动。母亲的病,必须用金线莲换来的钱治!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透。
林晚揣好那几株精心包裹、藏在最贴身衣物里的金线莲,
背着一个装着破衣服和一点干粮的旧挎包(作为去供销社的掩护),
告别了忧心忡忡的母亲,踏上了通往县城的土路。
几十里路,全靠双脚。林晚走得脚底磨出了水泡,又磨破了皮,火辣辣地疼。
汗水浸湿了衣服,又被风吹干,留下白花花的盐渍。
但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再快一点!把药换了,把钱带回去!
临近中午,风尘仆仆的林晚终于看到了县城低矮的城墙和灰扑扑的建筑。
她没有直接去供销社,而是在记忆中那个前世曾听老光棍提起过的、
靠近老汽车站后巷的区域转悠。那里人员混杂,是“黑市”的潜藏之地。
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尘土和一种说不清的紧张气息。
林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她看到一个缩在墙根下、面前摆着几个鸡蛋的老农,
一个挎着篮子、眼神飘忽的妇人,还有几个蹲在角落、低声交谈、目光警惕的汉子。
她深吸一口气,压下狂跳的心脏,学着那些人的样子,找了个相对僻静的角落蹲下来。
她没有直接把金线莲拿出来,而是先解开挎包,把里面那几件破衣服露出来一点,
装作是来卖旧衣物的样子。
眼睛却像雷达一样扫视着过往的行人,
寻找着可能的目标——那些看起来穿着体面些、或者脸上带着愁容、像是家里有人生病的人。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有人过来翻了翻她的破衣服,撇撇嘴走了。
有人好奇地打量她几眼。林晚的心沉甸甸的,手心全是汗。
难道没人识货?难道她记错了?难道这黑市已经没了?
就在她几乎要绝望的时候,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但明显是干部装样式的中山装、戴着眼镜、约莫五十多岁的清瘦男人,
皱着眉头,脚步匆匆地从巷口走过。
他的脸色有些憔悴,眼神里带着深深的焦虑,像是在寻找什么。
林晚的心猛地一跳!她想起了前世那个老光棍的话:
“……识货的,多是家里有病人,西医没办法,才偷偷摸摸找偏方的……”
她鼓起毕生的勇气,在那男人即将走过她面前时,
用极低、极快的声音,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
“大叔……要……好草药吗?治……咳喘的……”
那男人的脚步猛地顿住!
他锐利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般,瞬间锁定在蹲在角落、瘦小紧张的林晚身上!
林晚的心跳几乎停止,她能感觉到对方目光中的审视、怀疑,
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
“什么草药?”
男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克制,
但林晚敏锐地捕捉到了他语调深处的那一丝颤抖。
成了!有门!
林晚强压住激动,依旧低着头,用蚊子般的声音说:
“……金……金线莲,野生的,年份足……”
她不敢说太多。
男人的呼吸似乎急促了一瞬。
他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确认没人注意这边,然后飞快地蹲下身,声音压得更低:
“拿出来看看。快点!”
林晚的手微微颤抖着,从怀里贴身的地方,
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用旧报纸和苔藓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
她一层层剥开,露出了里面几株叶片细长、叶脉在昏暗光线下依然能看出淡淡金纹的鲜活植物。
那男人的眼睛瞬间亮了!
他凑近仔细看了看,甚至还拿起一株放在鼻尖轻轻嗅了嗅,
脸上露出一种混合着激动和难以置信的表情:
“……真的是野生的!品相……居然这么好?!”
他猛地抬头,目光灼灼地盯着林晚:
“小姑娘,你……你怎么卖?”
林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前世只知道这东西值钱,但具体值多少钱,
在这个年代的黑市该卖多少,她毫无概念!
说少了怕亏,说多了怕吓跑这唯一的买家。
她咬了咬牙,伸出两根手指,又犹豫了一下,再加了一根,用尽全身力气,
报出一个她自认为极其大胆的数字:
“三……三块钱……全要的话。”
这个价格,在这个普通工人月工资才二三十块的年代,绝对算是一笔“巨款”了!
她紧张地盯着男人的脸,生怕看到他拂袖而去的表情。
然而,那男人只是眉头紧锁,像是在衡量。
他看着林晚紧张得发白的小脸和破旧的衣服,又看了看手中那几株品相极佳的金线莲,
最终,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
“行!我全要了!”
男人飞快地从中山装内袋里掏出一个旧皮夹,数出三张一块钱的纸币,
又摸索出几张毛票,凑在一起塞到林晚手里,
“三块六毛二,我身上就这些了!快收好!”
他的动作快得像是在做贼,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