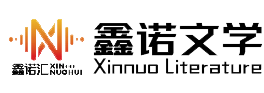然而,当张卫国回头看向自家炕上那个依旧昏迷不醒、浑身是伤的瘦小身影时,眼中充满了沉重的忧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敬意。林晚……你这丫头,用命搏出来的这条路,才刚刚开始。县里……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黑暗,如同粘稠的墨汁,无边无际地包裹着她。意识在深渊的边缘沉浮,时而能听到模糊的呼唤,像是隔着厚重的玻璃——“晚丫头…姐…”,时而又被尖锐的疼痛拽入更深的混沌。母亲的灰败的脸、王麻子怨毒的眼、荆棘刺破皮肉的冰冷、还有那沉甸甸的铁证……破碎的画面如同失控的走马灯,在意识的碎片里疯狂旋转。不知过了多久,一缕微弱的光,像针一样刺破了厚重的黑暗。林晚费力地掀开沉重的眼皮,刺目的光线让她瞬间眯起了眼。模糊的视线里,是低矮的、糊着旧报纸的房梁,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草药味和淡淡的血腥气。“醒了!姐醒了!”一个带着哭腔的童音在耳边炸响,是林小梅。紧接着,一张布满胡茬、憔悴不堪却写满惊喜和担忧的脸庞凑近了——是父亲林大山。“晚丫头!晚丫头!你感觉怎么样?别怕,爹在!”他的声音沙哑,带着劫后余生的颤抖。林晚张了张嘴,喉咙干涩得如同火烧,只发出嘶哑的气音。全身无处不在的疼痛瞬间清晰起来,尤其是后背和手臂,火辣辣地疼。她试图动一下手指,却牵动了伤口,疼得倒吸一口冷气。“别动!千万别动!”一个温和的女声响起,是张卫国的妻子,李婶。她端着一碗温热的米汤走过来,小心翼翼地用勺子沾湿林晚干裂的嘴唇,“醒了就好,醒了就好!丫头,你可是睡了整整三天三夜啊!吓死我们了!”三天三夜……林晚的意识渐渐回笼。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母亲的离世、孤身复仇、荆棘丛中的亡命奔逃、将证据交给张卫国……还有,张卫国在破晓时分,高举证据,当众审判王麻子的震撼场景!“娘……”她嘶哑地吐出第一个字,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林大山握住女儿冰凉的手,眼圈通红,声音哽咽:“你娘……你娘的后事,张队长帮着料理了……就葬在后山向阳坡……她说……喜欢那儿……”巨大的悲痛再次袭来,但这一次,林晚没有让自己沉溺。她闭上眼,泪水无声滑落,浸湿了鬓角。再睁开时,眼中虽然依旧盈满悲伤,却多了一份沉淀下来的坚毅。“爹……我没事……队长……队长呢?”她更关心张卫国和那些证据的下落。“张队长……”林大山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那天你昏倒后,张队长把王麻子捆得结结实实,带着那些……那些东西,当天就押着人去县里了!还没回来……”去县里了!林晚的心猛地一紧。县革委会,那是龙潭虎穴!王麻子在公社有靠山,在县里难保没有更深的关系!张卫国此去,是破釜沉舟,风险极大!“姐,你喝水……”林小峰端着一碗清水,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小脸上满是担忧和依赖。看着弟妹惊恐未消却强装镇定的样子,林晚压下心中的焦虑,努力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嗯,姐喝。”她小口啜饮着弟弟喂过来的水,温热的液体滋润了干涸的喉咙,也让她混乱的思绪稍稍清晰。身体的虚弱是实打实的。李婶解开她手臂上的绷带换药,那一道道被荆棘划开、深可见肉的伤口,皮肉翻卷,有的地方甚至化了脓,看得林大山这个汉子都别过了脸。脚底的伤更重,水泡磨破后感染,肿胀发亮。每一次清创换药,都如同酷刑。林晚死死咬着嘴唇,额头上冷汗涔涔,却一声不吭。这点痛,比起母亲的死,比起前世的业火,算得了什么?张卫国家成了她暂时的避难所。李婶尽心照顾,栓子婶也偷偷送过几次草药和鸡蛋,虽然依旧不敢明着来往,但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林晚记在心里。身体的恢复缓慢而痛苦,但林晚的意志如同岩石般顽强。她强迫自己进食,配合换药,哪怕疼得浑身发抖。第七天,她终于能勉强靠着被褥坐起来。窗外阳光正好,照在她苍白却异常平静的脸上。她看着弟弟妹妹笨拙地帮她端水、拿药,看着父亲沉默地坐在门槛上抽烟,佝偻的背影写满了沧桑和无力。这个家,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小船,在风暴过后,暂时搁浅在浅滩。掌舵的母亲走了,父亲这根桅杆也岌岌可危。现在,能撑起这艘船的,只有她了。就在这时,院门被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带着一身仆仆风尘走了进来,正是大队长张卫国!“队长!”“张队长!”林家几口人几乎同时出声,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充满了紧张和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