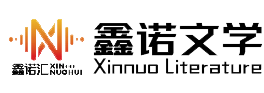洗菜的刘婶手一抖,菜掉进了盆里,溅起一片水花。纳鞋底的赵大娘动作也僵住了,眼神里充满了惊疑不定。周围的气氛瞬间变得诡异起来。“王老师……这话……可不能乱说……”有人小声嘀咕,带着怯意。“乱说?”王春梅提高了音量,带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你们想想,自从她跳了崖回来,家里出了多少事?她娘死了,她爹蔫了,她自己倒像换了个人!力大无穷,聪明绝顶!这不是邪门是什么?我听说啊,这种‘东西’,最克亲人!沾上谁,谁倒霉!”她的话,如同冰冷的毒液,迅速渗入那些妇人半信半疑的心田。恐惧的种子一旦种下,便开始疯狂滋长。看向林家方向的目光,渐渐带上了疏离和忌惮。这些风言风语,不可避免地吹进了林大山的耳朵。这个老实巴交、接连遭受丧妻、停职、女儿重伤打击的男人,精神早已绷紧到了极限。他像一头受伤的困兽,沉默地承受着一切。然而,“妖孽”、“克亲”、“邪术”这些字眼,如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击溃了他本就摇摇欲坠的心理防线。那天傍晚,林晚强撑着虚弱的身子,在灶台边用仅剩的一点玉米面熬糊糊。林小峰和林小梅懂事地在院子里帮忙劈一点细柴火。林大山则蹲在门槛上,对着渐渐暗下来的天色,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空洞而绝望。“爹,吃饭了。”林晚盛好三碗稀薄的糊糊,轻声唤道。林大山没有动,仿佛没听见。过了许久,他才猛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林晚,声音嘶哑而怪异,带着一种令人心寒的陌生感:“晚丫头……你……你告诉爹实话……你娘……是不是你克死的?”轰——!林晚只觉得脑子里一声炸响!手中的碗差点掉落!她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那个曾经用宽厚肩膀扛起这个家的男人,此刻眼中只有怀疑和恐惧!“爹!您说什么呢!”林小峰急得叫起来。“就是!姐不是妖孽!”林小梅也带着哭腔喊道。林晚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气血和瞬间涌上眼眶的酸涩。她放下碗,走到父亲面前,蹲下身,目光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直视着父亲那双被流言蜚语和巨大悲痛折磨得浑浊的眼睛:“爹,您看着我。”她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我是您闺女,林晚。娘走了,我心里的痛不比您少半分!我恨不能替娘去死!但我没死成,我活下来了。我活下来,不是为了被人戳脊梁骨骂‘妖孽’!是为了护着您!护着小峰小梅!护着娘用命换来的这个家!”她的声音微微发颤,带着刻骨的悲愤:“娘是病死的!是肺结核!是没钱治病,是被王麻子那畜生逼得断了活路才死的!跟什么‘妖孽’、‘邪术’有什么关系?!那些嚼舌根的话,您也信?!您是我爹!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您要是倒了,这个家就真的散了!娘在地下,能安心吗?!”林晚的话语,如同重锤,字字敲在林大山的心上。他看着女儿苍白却异常坚毅的脸庞,看着她眼中深沉的悲痛和不容置疑的守护决心,再看看旁边吓得瑟瑟发抖、却拼命维护姐姐的一双小儿女……浑浊的泪水终于从这个沉默汉子的眼中汹涌而出。“晚丫头……爹……爹糊涂啊!”林大山猛地抱住头,发出压抑已久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爹没用……护不住你娘……也护不住你们……爹……爹心里苦啊……”看着父亲崩溃痛哭的样子,林晚的心如同被刀绞。她伸出手,轻轻拍着父亲佝偻颤抖的背脊,声音柔和下来,却带着磐石般的坚定:“爹,哭出来就好了。日子再难,咱们一家人在一起,总能熬过去。流言蜚语伤不了人,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直!娘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她盼着我们好好活下去!”家庭的危机暂时在林晚的安抚下平息了,但村子里的暗流却愈发汹涌。王春梅的毒舌如同催化剂,让“妖孽”、“克亲”的流言越传越广,越传越邪乎。林晚走在村里,能明显感觉到那些躲闪的目光、压低的议论和无声的排斥。去井边打水,原本排着队的人会“恰好”让她先打;去自留地,相邻的田埂会莫名多出一道小土埂;连带着林小峰和林小梅去上学,也被一些不懂事的孩子远远地喊“小妖孽”……孤立和排斥,如同冰冷的潮水,无声地侵蚀着林家。林晚没有去争辩,没有去哭诉。她知道,在流言面前,任何解释都是徒劳,只会越描越黑。她只是更加挺直了脊背,眼神更加沉静。上课时,她加倍认真负责,用知识的光芒去驱散孩子们心中可能被植入的阴影;下课后,她主动帮助孙校长整理教案,打扫办公室;回到村里,她依旧礼貌地跟遇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哪怕对方只是冷淡地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