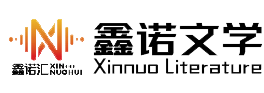然而,经济的枷锁依然沉重。母亲的药费像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林晚心头。代课老师的微薄补贴和补助,仅够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和弟妹的学费。她渴望给父亲买件厚实点的冬衣,给弟妹碗里添点油荤,更渴望存下一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她不能总靠张卫国的接济。深夜,煤油灯如豆。林晚伏在炕桌上,面前摊着那本几乎被翻烂的旧教材,旁边是她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草稿本。她不是在备课,而是在……写作。这个念头,源于几天前她在学校杂物间偶然翻到的一本卷了边角的旧杂志——《星火》。那是省里办的文艺刊物,上面登着一些反映农村新貌、知识青年下乡的诗歌、散文和小故事。林晚读着那些质朴却充满生活气息的文字,一个大胆的想法如同火花般在脑海中迸溅。她前世虽然是个混账,但也读过不少书,看过不少电影。更重要的是,她拥有两世为人的独特视角——她经历过七十年代农村的贫瘠与压抑,也见识过几十年后信息爆炸时代的繁华与思考。她熟悉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喜怒哀乐,那些沉默的汗水、坚韧的守望、在困苦中依然闪烁的人性微光……为什么不试试?用笔,记录下她所看到、所感受到的这个年代?用故事,去挣一份体面的收入?这个想法让她心跳加速。她仔细研究了《星火》的风格和要求,发现它偏爱扎根泥土、反映现实、基调积极向上的作品。她决定从最熟悉也最深刻的题材入手——乡村教师的坚守。一连几夜,当父亲和弟妹沉沉睡去,林晚便在摇曳的灯影下,用那支快磨秃了头的铅笔,在粗糙的草稿纸上,一笔一划地书写。她写自己初登讲台的忐忑与决心,写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纯真眼神,写深夜备课的孤灯,写看到学生进步时的巨大喜悦,也写面对流言蜚语时的委屈与倔强……她没有直接写王春梅事件,而是将那份压抑和抗争,巧妙地融入了主角面对工作困境时的心理描写。她给这篇散文取名为《讲台上的星光》。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朴实的叙述和最真挚的情感。她将重生后对教育、对生活、对守护的感悟,毫无保留地倾注其中。写完最后一个字,她看着厚厚一沓浸透着汗水和心血的稿纸,长长舒了一口气。无论结果如何,她尽力了。她小心翼翼地将稿纸誊抄在稍微干净些的本子上(用的是张卫国送的白纸),附上一封简短的信,说明自己是一名乡村代课教师,希望能得到编辑老师的指导。没有提家里的困境,只表达了想用文字记录乡村教育、传递正能量的愿望。信封上工整地写下《星火》杂志编辑部的地址,贴上珍贵的邮票。这封承载着希望的信,被她郑重地投进了公社邮局那个墨绿色的邮筒。等待的日子是漫长而焦灼的。林晚依旧每天认真上课,照顾家人,但眼神里多了一份不易察觉的期盼。她时常望向村口那条通往公社的土路,仿佛能看见邮递员绿色的身影。就在这份期盼中,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悄然降临。一天放学,林晚正收拾教案,一个穿着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蓝色青年装、戴着眼镜的清瘦年轻人出现在教室门口。他看起来二十出头,皮肤白皙,带着一种书卷气,与周围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请问……是林晚老师吗?”年轻人有些拘谨地开口,声音温和。“我是。您是?”林晚疑惑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我叫周卫民,是咱们公社新来的知青,分在隔壁前进大队。”年轻人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腼腆的笑容,“我……我听说您讲课讲得特别好,尤其是语文。我……我以前在城里也喜欢看点书,写点东西。现在响应号召下乡,也想……也想为村里的孩子们做点什么。所以冒昧来请教,不知道林老师方不方便……交流一下教学经验?”周卫民的态度诚恳而谦逊,眼神里充满了求知欲和对教育的热情。林晚心中一动。这个年代,能遇到一个同样热爱文学和教育的知青,实属不易。而且,对方来自前进大队,那里曾是王麻子的地盘,但现在……或许是一个新的开始?“周同志太客气了,请教不敢当,互相学习。”林晚露出真诚的笑容,将他请进了简陋的办公室。两人围绕着教材、教学方法、如何激发农村孩子学习兴趣等话题,竟越聊越投机。周卫民虽然年轻,但知识面很广,见解独到,对林晚提到的一些教学尝试(如用实物教学、编顺口溜记生字)大加赞赏。他甚至还带来了一本自己珍藏的、卷了边的《现代汉语词典》,表示可以借给林晚参考。“林老师,您的想法太好了!尤其是您说的,要把生活和知识联系起来!这比死记硬背强太多了!”周卫民眼中闪着光,“我在前进大队那边,孩子们基础更差,我正愁没办法呢!您可帮了我大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