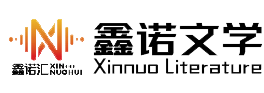第一章 寒夜启程
1975年的深冬,北中国仿佛被冻僵了。北风,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酷信使,裹挟着细碎的雪粒子,像无数根看不见的冰针,无孔不入地刮过林秀的脸颊。刺骨的寒意穿透了单薄的棉袄,直往骨头缝里钻。她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却只换来一阵更猛烈的哆嗦。车站昏黄的灯光在风雪中摇曳,将人影拉得扭曲而细长。
她紧紧攥着胸前,隔着厚厚的棉絮,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硬硬的方块轮廓——那是母亲临终前,用颤抖得不成样子的手,一针一线缝进棉袄内衬的油纸包。里面是三张皱巴巴、边缘磨损的粮票,还有一张早已泛黄、字迹晕染的信纸。那是父亲七年前寄回的最后一封信。她攥得那么紧,指关节都因用力而泛出青白色,仿佛这小小的包裹是她与这个世界仅存的、脆弱的联系。
“呜——!”一声凄厉刺耳的汽笛声,如同受伤野兽的嘶鸣,猛地刺破了风雪弥漫的夜空。巨大的、墨绿色的火车头喷吐着浓重的白烟,缓缓驶入站台,像一头疲惫不堪的钢铁巨兽。站台上瞬间涌动起来,提着大包小裹、扛着麻袋、背着铺盖卷的人们,如同潮水般涌向那敞开的、仿佛能吞噬一切的车门。
林秀深吸了一口气,那冰冷的空气灌入肺腑,带着煤灰和铁锈的味道,让她打了个寒噤。她将头上那条洗得发白、边缘磨损的蓝布头巾又用力裹紧了些,几乎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因惊恐和疲惫而显得格外大的眼睛。她随着人流,被推搡着、挤压着,艰难地挪向车门。混乱中,不知是谁的包袱撞到了她的腰,她闷哼一声,死死护住胸口,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挤上了那列开往未知南方的绿皮火车。
车厢里的景象比站台更令人窒息。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浓烈刺鼻的汗酸味、劣质烟草燃烧的呛人烟气、还有脚丫子、食物和不知名物品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气味,几乎让人作呕。狭窄的过道早已被行李和席地而坐的人占满。林秀被汹涌的人流推搡着,最终被死死地挤在车厢连接处的一个角落里。后背紧贴着冰凉、硬邦邦的车厢木板,前面是攒动的人头,她感觉自己像被嵌进了墙壁里,动弹不得。
她微微喘息着,目光茫然地扫过四周。对面座位上,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男人引起了她的注意。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膝盖上摊开一本用旧报纸仔细包着书皮的书,正低头专注地看着。昏黄的灯光落在他清瘦的侧脸上,显得安静而斯文。林秀下意识地将视线迅速移开,低下头,心脏在胸腔里怦怦直跳。她害怕,害怕被人看出自己眼底深藏的慌乱和恐惧,害怕被人盘问——毕竟在这个年代,一个年轻姑娘没有介绍信,私自离乡,形同逃窜,绝不是一件小事,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同志,要换座位吗?”一个温和的声音突然响起,像冬日里意外洒下的一缕暖阳,打破了林秀紧绷的思绪。
她猛地抬起头,正对上一双清澈、带着善意的眼睛。那男人约莫二十出头,面容清隽,军绿色棉袄虽然旧,却洗得干干净净,胸前一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在灯光下闪着微光。他看着她,眼神里没有探究,只有关切。
林秀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应。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她习惯了警惕,习惯了沉默。
男人却轻笑了一声,那笑容很干净,带着点书卷气:“我去车厢连接处透透气,你站得太辛苦了,先坐会儿吧。”不等她拒绝,他已经利落地合上书,站起身,动作敏捷地挤过拥挤的人群,消失在通往连接处的门后。
车厢里依旧嘈杂混乱,但林秀望着那个空出来的座位,心头却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暖流。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坐了下去。硬邦邦的木头座位并不舒服,但比起站着,已是天壤之别。火车在一声悠长的汽笛中缓缓启动,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单调而沉重的“哐当、哐当”声。
林秀将头轻轻靠在冰冷的车窗上,目光失焦地望着车窗外飞速掠过的、被冰雪覆盖的荒原。脚下结着薄冰的地面反射着幽光。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三天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傍晚。
破败的土屋,昏暗的煤油灯。母亲躺在炕上,发着骇人的高烧,整张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得像破风箱。剧烈的咳嗽撕扯着她的胸腔,每一次咳喘,摊在枕边的手帕上就洇开一片刺目的血渍。屋门就是在那时被粗暴地踹开的。冷风和雪粒子猛地灌了进来。
两个穿着洗得发灰中山装、臂戴红袖章的男人闯了进来,带着一身室外的寒气和不近人情的戾气。为首的男人眼神冰冷,声音像是淬了冰:“周建国家属!周建国在西南边境执行任务时思想动摇,犯了严重错误!组织决定,没收你们家所有存粮!”
母亲像被雷击中,挣扎着想从炕上爬起来,枯瘦的手死死抓住炕沿,声音嘶哑地争辩:“不…不可能…建国他…他是好人…粮…粮食是孩子的命啊…”她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其中一个红袖章不耐烦地一把推开。本就虚弱不堪的母亲像一片枯叶般摔倒在地,头重重地磕在桌角上,发出一声沉闷的钝响。殷红的血,瞬间染红了斑驳的地面。
林秀尖叫着扑过去,却被另一个红袖章死死拦住。他们粗暴地搬走了米缸里所剩无几的粮食,甚至搜走了灶台角落藏着的半袋玉米面。母亲躺在冰冷的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房梁,气息越来越微弱,最终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寒夜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连一句遗言都没能留下。
“下一站,江州!有下车的旅客请做好准备!”列车员带着浓重口音的报站声,如同惊雷般将林秀从痛苦的回忆深渊中猛然拉回现实。
她浑身一颤,下意识地伸手紧紧按住胸口——隔着棉袄,那个硬硬的油纸包还在。她摸了摸,指尖仿佛能感受到信纸上父亲那刚劲有力的字迹。那是父亲七年前最后一封信的地址。信里,他提到江州纺织厂有位姓陈的工友,为人仗义,或许能帮她找到在西南边境“执行任务”后便下落不明、音讯全无的父亲。“去找陈德海叔叔”,这是母亲弥留之际,用尽最后力气叮嘱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