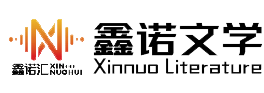巨大的断裂声和铁屑飞溅的场面,让整个车间瞬间陷入一片混乱!惊呼声、尖叫声响成一片!附近的工人纷纷惊恐地后退。
“怎么回事?!谁干的?!”赵永年主任脸色铁青,像一阵风似的冲到三号机台前,看着断裂的传送带和一片狼藉的地面,额头上青筋暴跳。他的目光像两把刀子,狠狠地剜向被王建军扶起来、惊魂未定、脸色惨白的林秀,声音冰冷得能冻死人:“林秀!谁让你擅自检查机器的?!啊?!刚来就给我捅这么大篓子!破坏生产!耽误军工任务!这罪名你担得起吗?!”
林秀被这劈头盖脸的指责砸懵了,巨大的恐惧和后怕让她浑身发抖。但她强忍着,指着还在兀自冒烟、发出不规律异响的机台,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清晰:“主…主任!不是…不是我的问题!是机器!这台机器本来就有问题!您看,纱线张力严重不均,齿轮咬合的声音也不对!我…我只是想看看……”
“够了!”赵永年粗暴地打断她,猛地摘下金丝眼镜,用一方雪白的手帕用力擦拭着镜片。当他重新戴上眼镜时,镜片后的那双三角眼里,闪烁着毫不掩饰的阴鸷和狠厉。“巧舌如簧!推卸责任!我看你就是思想有问题!存心来搞破坏的!来人!”他猛地一挥手,声音陡然拔高,“把她给我带到保卫科去!好好审问!”
两个早已候在一旁、臂戴红袖章、神情凶悍的保卫科干事,立刻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一左一右架住了林秀的胳膊!
“等等!主任!请等一下!”一个清朗而急切的声音穿透了混乱!陆远不知何时冲进了车间,奋力拨开人群。他高高举起手中的一个硬皮笔记本,声音因为激动和奔跑而有些喘息,却异常清晰有力:“我有证据!我有证据证明这绝不是人为事故!更不是破坏生产!”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这个突然闯入的年轻大学生身上。赵永年眯起了眼睛,闪过一丝惊疑。
陆远快步走到赵永年面前,翻开笔记本,指着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数据和几处明显的齿轮油污痕迹:“我连续三天,利用课余时间,在车间外围的不同时段,记录了包括三号机台在内的几台关键设备的噪音分贝、震动频率和纱锭转速波动情况!根据我的记录和初步分析,三号机台的轴承磨损率超出安全标准值三倍以上!齿轮啮合间隙过大!早就该停机报修了!今天的事故,完全是设备严重老化、长期带病运行导致的必然结果!跟这位新来的林秀同志没有任何关系!她发现问题,想检查,恰恰说明她认真负责!”
陆远的话像一颗炸弹在车间里炸开!工人们顿时一片哗然,议论纷纷。大家早就对车间一些老设备的状况心知肚明,只是敢怒不敢言。此刻被一个“外人”当众点破,看向赵永年的目光都变得复杂起来。
赵永年的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青一阵白一阵,像开了染坊。他死死盯着陆远手中的笔记本,又看了看周围工人们窃窃私语、隐含不满的神情,腮帮子咬得紧紧的。过了好几秒,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带着浓浓的不甘和阴冷:“哼!既然是…设备本身的问题…那…”他挥了挥手,像驱赶苍蝇一样,“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去!维修班!立刻给我修好三号机台!耽误了任务,唯你们是问!”
他临走前,目光像毒蛇一样,再次狠狠剜了林秀和陆远一眼。那双锃亮的皮鞋跟,仿佛带着无尽的怨毒,重重地碾过地上散落的、还带着机油味的断裂铁屑,发出令人心悸的摩擦声,然后才转身离去。
傍晚,下工的铃声终于响起。林秀拖着疲惫不堪、依旧有些发软的身体走出车间。寒风一吹,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王建军从后面追了上来,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迅速将一个温热的油纸包塞到林秀手里,压低声音:“给,拿着。看你中午没去食堂,偷偷给你留了两个白面馒头。”
林秀看着手中的馒头,心中五味杂陈。她低声道谢:“谢谢王师傅。”
王建军凑得更近了些,声音压得更低,眼神里带着一丝后怕和忧虑:“小周…今天多亏了那个大学生…不过,你还是要小心那个赵主任!”他顿了顿,似乎下了很大决心,声音几不可闻:“我听说…听说他跟当年那批军工物资失踪案…好像有点不清不楚的瓜葛…你…”
话没说完,一阵急促而嚣张的摩托车轰鸣声由远及近,在车间门口戛然而止!
林秀的心猛地一跳,下意识地透过车间巨大的玻璃窗向外望去。只见三个穿着笔挺灰色中山装、气势不凡的男人正从摩托车上下来。赵永年早已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点头哈腰地迎了上去。为首的那个中山装男人身材高大,面容冷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脚上那双擦得锃亮的皮靴——靴帮上沾着几块暗红色的、像是干涸血迹的泥土污迹!更让林秀瞳孔骤缩的是,他腰间皮带上别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皮匣子!虽然被大衣下摆遮住大半,但那硬朗的轮廓和偶尔露出的金属搭扣,在暮色中隐隐泛着冰冷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幽光!
当那个为首的男人侧过身,似乎在听赵永年汇报什么时,他胸前别着的那枚毛主席像章,在夕阳余晖下清晰地映入林秀的眼帘——那特殊的造型、边缘的纹路,与她在家中唯一保存下来的父亲照片里,那个带队闯入她家、最终导致母亲身亡的红袖章男人所佩戴的像章,几乎一模一样!
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从林秀的脚底板直冲头顶!她下意识地抓紧了手中的馒头,指尖深深陷入松软的面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