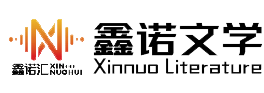张秘书的眼神充满了紧迫感:“但是!刘主任也警告,赵永年狗急跳墙了!他今晚就要把最后一批没来得及转移的物资和所有证据彻底销毁!你们必须阻止他!立刻去!晚了就来不及了!我…我这就想办法去联系省里的同志!快走!”
希望之火再次点燃!带着焚烧一切的愤怒!林秀猛地站起身,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泥水,紧紧抱住怀里的铁盒!陆远!必须立刻找到陆远!
当林秀找到陆远,将陈德海用命换来的铁盒和张秘书的话告诉他时,陆远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锐利。他没有丝毫犹豫:“走!去锅炉房!”
深夜的纺织厂旧锅炉房区域,早已废弃多年,如同巨大的钢铁坟墓。巨大的炉体锈迹斑斑,管道扭曲断裂,地面上积着厚厚的煤灰和油污。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煤烟味、铁锈味和浓重的灰尘气息。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远处投下惨淡的光晕。
林秀和陆远打着手电筒,如同两只灵巧的猫,悄无声息地潜入了这片黑暗的领地。巨大的炉壁投下狰狞的阴影。按照张秘书的指示,他们找到了最里面靠西的墙根。墙面是粗糙的青砖砌成,布满了厚厚的煤灰。
“第七排…第三块…”陆远低声数着,手指在冰冷的砖面上划过。他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多功能小刀,小心翼翼地撬动着那块砖的边缘。砖块果然有些松动!两人合力,屏住呼吸,一点点地将那块沉重的青砖从墙缝里抽了出来!
一个黑洞洞的、仅能容下一个铁盒的凹槽露了出来!陆远伸手进去,果然摸到了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他用力一拽——一个沉甸甸的、同样锈迹斑斑的长方形铁盒子被取了出来!
就在陆远撬开铁盒搭扣,借着微弱的手电光,看到里面那几本厚厚的、写满密密麻麻数字和人名的账本,以及几张清晰的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正是赵永年和一个刀疤脸男人举杯的合影)时——
“轰隆隆!”巨大的卡车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刺眼的车灯光柱猛地扫射过来,将整个锅炉房区域照得亮如白昼!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东西交出来!”赵永年那充满怨毒和暴戾的声音在黑暗中炸响!他和七八个手持棍棒、砍刀甚至手枪的凶悍打手,如同鬼魅般从卡车后面和周围的阴影里涌了出来,瞬间将林秀和陆远团团围住!黑洞洞的枪口在灯光下泛着死亡的光泽!
千钧一发!生死一线!
“呜哇——呜哇——呜哇——!!!”
比之前更加密集、更加嘹亮、仿佛要撕裂夜空的警笛声,如同天籁之音,骤然划破死寂!四面八方!由远及近!如同潮水般涌来!刺眼的红蓝警灯瞬间将整个厂区映照得如同白昼!
“不许动!警察!”
“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你们被包围了!”
大批穿着藏蓝色制服、手持冲锋枪的公安干警,如同神兵天降,从各个方向冲了出来!警车将整个锅炉房区域围得水泄不通!省厅的专案组到了!
赵永年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随即变成极致的恐惧和绝望!他脸色惨白如死人,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凶光!他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漆黑的手枪,歇斯底里地吼道:“老子跟你们拼了!”枪口赫然指向了离他最近的陆远!
“砰!”一声枪响!
然而倒下的却不是陆远!
就在赵永年扣动扳机的瞬间,一个浑身是血、如同血人般的身影,如同愤怒的雄狮,猛地从一辆卡车的阴影里扑了出来,用尽最后的力量狠狠撞在赵永年的后腰上!
“老狗!去死吧!”是陈德海!他竟然挣扎着追到了这里!
赵永年被撞得一个趔趄,枪口一歪,子弹擦着陆远的耳边呼啸而过,打在旁边的炉壁上,溅起一串火星!而陈德海则因伤势过重和巨大的撞击力,重重地摔倒在地,生死不知!
“陈叔!”林秀发出凄厉的哭喊。
“拿下!”公安干警如猛虎下山,瞬间将负隅顽抗的赵永年及其爪牙全部制服!冰冷的手铐锁住了那双沾满罪恶的手。
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穿透云层,驱散黑暗,照亮整个江州城时,林秀站在家中那张唯一的、父亲穿着旧军装的遗像前。照片上的父亲,眼神依旧坚毅地望着远方。她颤抖着手,将陈德海用生命守护下来的那枚残缺的、染血的军功章,还有从锅炉房砖缝里找到的、记录着赵永年滔天罪证的账本,轻轻地、庄重地放在了供桌之上。
陆远静静地站在她身旁,手中拿着那份刚刚送达的、盖着鲜红大印的《关于为周建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书》。他的声音温和而有力:“下个月,市里要为当年所有受冤屈、被迫害的同志,召开隆重的平反昭雪暨表彰大会。你父亲的名字,将在阳光下,被所有人铭记。”
林秀缓缓转过头,望向窗外。纺织厂上空,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正在晨风中猎猎作响,舒展飘扬。那些笼罩了她整个青春、迷雾重重的黑暗过往,那些浸透了血泪的冤屈和痛苦,终于在这一刻,被这初升的朝阳彻底驱散,化作了历史的尘埃。
而属于林秀的,挣脱了枷锁、充满了无限可能的,崭新的人生画卷,才刚刚在这片洗刷了污浊、洒满阳光的大地上,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