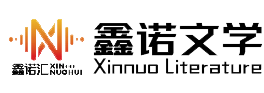当舔狗停止供养
我给总裁当了七年舔狗,他生日宴上却当众踩碎我的蛋糕。
“你这种底层蝼蚁,也配碰我的东西?”
回家路上头痛欲裂,记忆突然全部解锁。
原来这些年我像程序般精准讨好他,全是脑内芯片强制执行的指令。
第二天总裁浑身抽搐地爬进我家。
医生诊断报告显示:他的生理机能已完全依赖我分泌的血清素。
“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他嘶吼着抓住我的裤脚。
我微笑着蹲下,像抚摸流浪狗般拍了拍他的脸。
“顾总,现在轮到你当舔狗了。”
“不过——”
我起身关紧防盗门。
“我嫌脏。”
雨,敲打着出租车蒙尘的车窗,细密又冰冷,在玻璃上蜿蜒出扭曲的光带。
窗外,城市华灯初上,霓虹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流淌,汇成一片模糊而刺眼的斑斓光海。
车内弥漫着一股廉价香氛与旧皮革混杂的、令人窒息的沉闷气味。
我蜷在后座角落,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蛋糕盒,硬纸壳的边缘硌着我的肋骨,冰冷而坚硬。
盒子里装着顾琛的生日蛋糕。七寸,黑森林。
不是蛋糕店橱窗里那些流水线产品,而是我亲手做的,
在狭小出租屋的厨房里忙活了整个周末。
融化进口黑巧的苦涩气息似乎还萦绕在指尖,混合着樱桃利口酒的甜香。
我甚至记得自己笨拙地裱花时,手腕微微颤抖的触感——生怕有一丝不完美。
这双手,为他熨烫过无数件衬衫,熬过数不清的夜,
此刻却僵硬地环抱着这个可笑的盒子,像个护着救命稻草的溺水者。
记忆像个不怀好意的窃贼,悄然溜回几个小时前那个金碧辉煌的宴会厅。
水晶吊灯的光芒璀璨得刺眼,把每一个人的笑容都照得虚浮失真。
空气里浮动着高级香槟的清冽、昂贵雪茄的醇厚,还有女士们身上挥之不去的奢侈香水味。我穿着唯一一套能撑场面的、洗得有些发白的西装,
像个误入天鹅群里的丑小鸭,局促地站在奢靡的光影边缘。
目光穿过衣香鬓影的人群,精准地锁定了被簇拥在中央的顾琛。
他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深色礼服,身姿挺拔如松,
正漫不经心地晃动着手中的水晶杯,琥珀色的酒液折射着璀璨的光。
侧脸的线条依旧冷峻完美,带着一种睥睨众生的疏离感。
我的心跳,在那个瞬间,又不争气地加快了节奏,
每一次搏动都沉重地撞击着肋骨,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献祭般的悸动。
鼓足勇气,我挤出人群,走向那个光芒的中心。
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又像踏在烧红的烙铁上。
周围那些探究的、嘲弄的、鄙夷的目光,像无数根细小的针,
密密匝匝地扎在我裸露的皮肤上。
我努力挺直背脊,捧着那个精心呵护的蛋糕盒,像捧着自己卑微跳动的心脏,走到他面前。
“顾总,”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在喉咙里艰难地滚动,
“生日快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周遭的谈笑似乎停滞了一瞬。
顾琛缓缓转过身,那双深邃的眼眸扫过来,没有任何温度,
如同冰冷的探照灯,带着审视和一丝毫不掩饰的厌烦。
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又滑落到我怀中的蛋糕盒上,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勾起一个弧度。
那不是微笑。那是冰层裂开一道缝隙,露出底下彻骨的寒。
“哦?”他低沉的嗓音带着一丝玩味,像冰冷的丝绸拂过耳膜,“陈默?你怎么混进来的?”
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甚至能感觉到血液冲上脸颊的灼热感,像被当众抽了一记耳光。
“我……”喉咙像被砂纸堵住,所有准备好的祝福词瞬间蒸发,“我听说您今天……”
“心意?”他打断我,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种刻骨的轻蔑。
他抬起脚,那只锃亮的、价值不菲的意大利手工皮鞋,
在我惊愕的目光中,带着一种慢镜头般的、残忍的优雅,
稳稳地、狠狠地踩在了蛋糕盒的正中心!
“咔嚓!”
硬纸壳瞬间塌陷、碎裂!蛋糕盒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鲜奶油和深色的巧克力蛋糕胚从破损的缝隙里猛地爆裂出来,像被践踏的内脏。
一块沾着酒渍樱桃的奶油,飞溅起来,不偏不倚,
正好砸在我那双穿了很久、边缘已经微微开胶的旧皮鞋面上。
“你这种底层爬出来的蝼蚁,”顾琛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了瞬间死寂的空气,
每一个字都淬着冰渣,精准地钉入我的耳膜,“也配碰我的东西?”
他收回脚,鞋底沾着一点刺眼的奶油。
他甚至没有再多看我一眼,仿佛只是随意碾死了一只碍眼的虫子,
转过身,继续和旁边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谈笑风生。
那女人捂着嘴,发出一声压抑的嗤笑。
周围的目光瞬间变得赤裸而滚烫,混杂着毫不掩饰的鄙夷和猎奇般的兴奋,
像无数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皮肤上。
世界骤然失声,只剩下我胸腔里那颗心脏疯狂擂动的声音,震耳欲聋,
带着一种濒死的窒息感。血液在瞬间冻结,又在下一秒疯狂地逆流冲上头顶,眼前阵阵发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