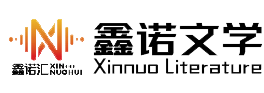羞辱。铺天盖地、足以将人溺毙的羞辱。
我几乎是凭着本能,在那些锥子般的目光将自己彻底钉穿之前,
狼狈地转身,像逃离地狱般冲出了那片令人作呕的光鲜亮丽。
身后似乎传来几声模糊的哄笑,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背上。
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和滚烫的液体混合在一起,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我死死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一丝腥甜的铁锈味,才勉强抑制住喉咙里翻涌的呜咽。
耻辱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着我的心脏,越收越紧,几乎要将它勒碎。
七年。
整整七年。
我像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精准地、不知疲倦地围着他转。
他随口一句“咖啡冷了”,我能在凌晨三点跑遍半个城市找一家营业的精品咖啡店;
他一个皱眉,我就能立刻解读出他所有未说出口的烦躁,
然后像个卑微的清洁工一样,小心翼翼地替他扫清所有障碍;
他生病时,我守在床边,彻夜不敢合眼,
比最专业的护工还要细致体贴……我的世界,我的时间,我的喜怒哀乐,
全都以他的意志为轴心运转。
付出一切,燃烧自己,只为换取他一个偶尔投来的、漫不经心的眼神,
或是施舍般的一句“还行”。
这难道不是爱吗?那种卑微到尘埃里、开不出一朵花的爱?
可刚才那被当众踩碎的蛋糕,那如同垃圾般被丢弃的尊严,
像一把生锈的钝刀,狠狠地捅进了这个自我催眠的幻梦里,搅得血肉模糊。
一个清晰得可怕的声音在脑海里尖啸:
陈默,你他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可救药的舔狗!
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人家连正眼都懒得看你!
这个认知带来的痛苦,比刚才当众的羞辱更甚百倍。
胃里一阵剧烈的翻搅,我猛地捂住嘴,强忍着呕吐的冲动,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道月牙形的血痕。
出租车终于停在老旧的居民楼下。
我几乎是滚下车,踉跄着冲进弥漫着潮湿霉味和油烟气的楼道。
声控灯年久失修,光线昏暗闪烁,在斑驳脱落的墙皮上投下鬼魅般的影子。
扶着冰冷肮脏的楼梯扶手,一步,两步……每一步都沉重得像拖着灌铅的脚镣。
钥匙在锁孔里颤抖着转动了好几次,才终于打开了那扇单薄的、锈迹斑斑的防盗门。
“砰!”
门在身后重重关上,隔绝了外面淅沥的雨声和整个世界。
狭小的出租屋瞬间被沉甸甸的黑暗吞噬。
我没开灯,背靠着冰冷的门板,身体沿着粗糙的木质纹理无力地滑落,
最终瘫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怀里那个破碎的蛋糕盒“啪嗒”一声掉落在脚边,
粘腻的奶油和蛋糕残骸在地板上摊开一小片狼藉,散发出甜腻又绝望的气息。
黑暗像粘稠的墨汁,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
七年的记忆碎片,如同被按下了快进键的默片,在眼前疯狂闪回。
——为他熬夜整理商业报告,窗外天色泛白,他接过时只冷淡地“嗯”了一声。
——跑遍全城买他随口提过的限量版钢笔,双手奉上,他随手扔进抽屉深处。
——他醉酒后拨错电话,我狂奔几条街把他从酒吧街背回公寓,
他醒来后皱着眉:“谁让你多管闲事?”
——生日、节日、纪念日…每一次精心准备的礼物或惊喜,
换来的都是他习以为常的漠然,甚至是不耐烦的挥手驱赶,像赶走一只嗡嗡叫的苍蝇……
每一个画面,每一次付出,每一次被轻贱、被忽视、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瞬间,
都在此刻被无限放大、扭曲,带着尖锐的嘲讽,一遍遍刮擦着我早已千疮百孔的自尊。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反复揉捏蹂躏,每一次收缩都带来撕裂般的剧痛。
呼吸变得困难,每一次吸气都像吞下滚烫的沙砾,灼烧着喉咙和肺叶。
“为什么……” 一个沙哑、不成调的声音从我齿缝里挤出,
带着浓重的血腥气,“陈默……你他妈到底为了什么啊……”
仿佛是为了回应这绝望的诘问,一股难以形容的剧痛毫无征兆地在我头颅深处猛烈炸开!
“呃啊——!”
我闷哼一声,身体猛地弓起,额头狠狠撞在冰冷的门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那感觉,就像有人用一把烧红的铁钎,从我的太阳穴狠狠捅了进去,然后在脑浆里疯狂搅动!视野瞬间被一片刺眼的白光占据,无数破碎扭曲的噪点疯狂闪烁,
耳边是尖锐到极致的、足以撕裂灵魂的蜂鸣!
剧痛如同海啸,一波强过一波,无情地冲击着意识最后的堤坝。
无数被尘封的、被遗忘的、甚至是被强行扭曲的记忆碎片,在这毁灭性的剧痛中,
被硬生生地从意识的最底层撕扯出来,带着血淋淋的真相,轰然冲垮了所有自欺欺人的堤防!
那不是爱!从来都不是!
那是……冰冷的代码!是设定好的程序!
是植入大脑深处、无时无刻不在强行扭曲我意志的……芯片!
一幅清晰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在剧痛的白光中浮现:冰冷的金属手术台,刺眼的无影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