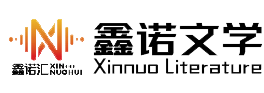戴着口罩的模糊人影,手中拿着闪烁着幽蓝冷光的、细如发丝的探针……画面一闪而过,
随之而来的是无数个瞬间的回放:
——当顾琛皱眉时,大脑皮层深处某个区域瞬间被激活,强制释放出焦虑和担忧的化学信号,驱使我立刻去解决“问题”。
——当他表现出哪怕一丝丝正面反馈(哪怕只是没有斥责),
另一个区域立刻被刺激,释放出超乎寻常的欣快感和多巴胺,像给机器狗投喂的奖励。
——而当我的自尊心试图抬头,当我内心产生一丝反抗或质疑的念头时,
一股强烈的、足以瞬间摧毁意志的剧痛便会立刻降临,
如同最严厉的惩罚程序,精准地扼杀任何“叛逆”的苗头。
七年!整整七年!我像一个被输入了核心指令的傀儡!
我的喜怒哀乐,我的卑微付出,我燃烧自己照亮他的全部人生……所有的一切,
都不过是那枚嵌入我颅骨深处的冰冷芯片,在强制执行的既定程序!
“嗬……嗬……” 我蜷缩在地板上,
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痉挛,喉咙里发出濒死野兽般的嗬嗬声。
冷汗瞬间浸透了单薄的衬衫,黏腻冰冷地贴在皮肤上。
极致的痛苦与颠覆性的真相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我的灵魂彻底撕裂。
眼前阵阵发黑,意识在崩溃的边缘摇摇欲坠。
不知过了多久,那足以摧毁灵魂的剧痛如同退潮般缓缓散去,
留下的是深入骨髓的疲惫和一片冰冷的死寂。
大脑里仿佛经历了一场核爆,硝烟弥漫,残骸遍地。
我瘫在地上,像一具被抽空了骨头的皮囊,只有胸膛还在微弱地起伏。
汗水浸透了头发,黏在冰冷的额角。
眼前依旧是模糊的,但那种被操控的混沌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残忍的清明。
我慢慢地、极其艰难地抬起一只手,颤抖着摸向自己的后脑勺。
发根深处,靠近颅骨底部的位置……指尖触碰到一小块极其微小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凸起。冰凉的,坚硬的,像一颗深埋在血肉里的微型骨刺。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它,像一根无形的提线,操纵了我整整七年的人生!
让我心甘情愿地匍匐在顾琛脚下,做一条摇尾乞怜、毫无尊严的狗!
一股冰冷的、足以冻结血液的寒意,瞬间从尾椎骨窜上头顶。
紧接着,是滔天的怒火!
那火焰并非灼热,而是极致的、带着毁灭气息的寒冷,瞬间席卷了四肢百骸!
我猛地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入掌心,尖锐的刺痛感传来,却丝毫压不住那焚心蚀骨的恨意!
顾琛!那个高高在上、视我如蝼蚁的男人!他一定知道!
他绝对知道这一切!是他!是他把我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是他窃取了我的人生,践踏了我的灵魂!
复仇的念头,像一颗剧毒的种子,在这片被恨意彻底冰封的土壤里,
瞬间破土而出,疯狂滋长!我要让他付出代价!
付出他无法想象的、刻骨铭心的代价!
就在这恨意燃烧到顶点之时——
“砰!砰!砰!”
沉重的、混乱的撞击声,粗暴地撕裂了出租屋的死寂!
不是敲门,更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在一下下、毫无章法地撞在单薄的防盗门上!
伴随着一种压抑的、仿佛从喉咙深处硬挤出来的、介于呜咽与嘶吼之间的诡异声响。
“呃……呃呃……”
那声音……极度痛苦,极度扭曲,带着一种非人的挣扎感。
我猛地从地上撑起身体,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撞击。
是谁?这破旧的筒子楼里,谁会在这个时间,以这种方式……撞我的门?
一股莫名的寒意顺着脊椎爬升。
我扶着冰冷的墙壁,踉跄着站起来,双腿还有些发软。
一步一步,挪到门边。
透过门板上那个小小的、模糊的猫眼,小心翼翼地向外望去。
楼道里那盏接触不良的声控灯,正忽明忽灭地闪烁着,投下惨白又摇曳的光影。
就在那明明灭灭的光线下,一个人影蜷缩在我门前的水泥地上。
昂贵的、沾满污渍的黑色羊绒大衣裹着身体,
但那身体此刻却在剧烈地、不受控制地抽搐着!
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每一次痉挛都扭曲成一个诡异的角度。
苍白的脸上布满冷汗,头发凌乱地黏在额角,
曾经冷峻完美的五官因为极度的痛苦而完全扭曲变形,眼白里布满了狰狞的血丝。
他抬起头,试图看向猫眼的方向,
嘴唇剧烈地哆嗦着,发出意义不明的“嗬……嗬……”声,
涎水不受控制地从嘴角淌下,在下巴上拉出一道亮晶晶的、恶心的水痕。
顾琛!
那个几个小时前还在宴会厅里光芒万丈、视我如草芥的顾氏总裁顾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