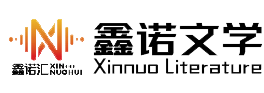我缓缓地、慢慢地蹲了下来。
蹲在顾琛的面前,蹲在这条曾经不可一世、此刻却只能在我脚下垂死挣扎的“狗”的面前。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快意,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冰冷的平静。
我伸出右手,动作甚至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柔”,轻轻地、像抚摸一件易碎品般,
拍了拍他那张布满冷汗、因痛苦和极度恐惧而扭曲变形的脸颊。
指尖传来的触感冰冷、粘腻,带着濒死的颤抖。
“顾总,”我的声音很轻,很平,像在陈述一个无关紧要的事实,
却清晰地穿透了他痛苦的喘息和医生的惊呼,
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精准地钉入他的耳膜,“现在,轮到你当舔狗了。”
顾琛的身体在我手下猛地一颤,血红的眼睛瞬间瞪大到极致,
里面翻滚着难以置信、滔天恨意和一种被彻底打入深渊的、终极的恐惧。
我慢慢地站起身,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
他那只抓住我裤脚的手,因为剧烈的抽搐已经无力地滑落,瘫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不过——”
我微微侧过头,目光扫过他抽搐的身体,扫过他绝望的眼睛,
嘴角极其缓慢地向上勾起一个冰冷的、毫无温度的弧度。
“我嫌脏。”
话音落下的瞬间,我没有任何停顿,身体向后一步,退回了门内。
“不……不!!!” 顾琛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喉咙里爆发出最后一声绝望到撕裂的、非人的嚎叫!
“砰——!”
沉重的、锈迹斑斑的防盗门,带着一种冰冷而决绝的金属质感,在我面前被猛地关上。
门轴发出一声刺耳的、令人牙酸的摩擦声。
最后映入我眼帘的,是顾琛那只伸向门缝方向、徒劳抓握着空气的、剧烈痉挛的手。
指尖在惨白的灯光下泛着死灰色。
然后,是彻底的黑暗和死寂。
门板隔绝了外面的一切声音。那绝望的嘶嚎,那痛苦的抽搐,
那医生惊慌失措的低喊……所有的噪音都被这扇冰冷的铁门阻挡在外。
狭小的出租屋里,只剩下我自己的呼吸声,平稳,悠长,
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劫后余生般的空旷感。
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站了一会儿。
黑暗像温柔的潮水,包裹着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天剧变的灵魂。
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那个破碎蛋糕散发出的、甜腻又绝望的气息。
没有开灯。
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走向屋里那张简陋的桌子。
借着窗外城市遥远霓虹投进来的、微弱而迷离的光线,我的目光落在桌上。
那里,静静地立着一个东西。
一个深褐色的、方方正正的玻璃瓶。
瓶身上没有任何标签,只有瓶口处残留着一点暗红色的、已经凝固的液体痕迹。
在昏暗中,那点暗红像凝固的血,散发着一种不祥的、幽冷的光泽。
我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冰冷的玻璃瓶身。
然后,稳稳地、没有丝毫颤抖地,将它握在了手中。
2. 冰冷的门板隔绝了门外垂死的挣扎与绝望的嘶吼,
3. 也隔绝了那个曾经占据我全部世界的男人。
4. 出租屋重新沉入一片死寂,只有我胸腔里那颗心脏,
5. 缓慢而沉重地搏动着,每一次跳动都带着一种崭新的、陌生的回响。
空气里甜腻的蛋糕味混合着尘埃的气息,像一场荒诞剧落幕后的余烬。
我没有回头,只是背靠着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感受着门板传来的、微弱而断续的撞击震动——那是顾琛垂死身体最后的抽搐,
如同困兽绝望的撞击。
每一次震动,都清晰地传递过来,像敲打在灵魂上的鼓点。
七年。被操控的七年。
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卑微的讨好,都不过是芯片冰冷的指令。
而门外那个正在腐烂的男人,就是这一切的根源,
也是这指令的最终受益者——一个建立在他人血肉之上的寄生者。
恨意,不再像之前那样灼热沸腾,而是沉淀下来,
凝结成一种更坚硬、更冰冷的东西,沉甸甸地压在心底。
窗外的霓虹光影透过蒙尘的玻璃,在昏暗的地板上投下变幻莫测的光斑。
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那张摇摇晃晃的旧木桌上。
它静静地立在那里。
深褐色的玻璃瓶,瓶身没有任何标签,
在微弱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不透明的、深沉的质感。
瓶口处,一圈暗红色的、粘稠的液体凝固物,像干涸的血迹,
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金属腥气和某种奇异甜香的气味。